荆州网络营销推广(「以案释法」销售VPN“翻墙”软件是否构成犯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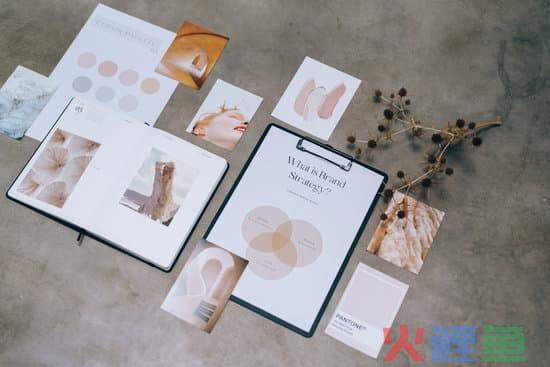
一、朱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在本案中,行为人朱某于荆州市荆州区设立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并创建多个网站用以销售其代理或自行建立的VPN“翻墙”软件。从本罪出发,对朱某的构罪评价主要集中在其没有按照《电信条例》的有关规定获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以及在监管部门——荆州市公安局做出关停VPN业务的通知后,拒不关停继续销售VPN“翻墙”软件的行为上。
「以案释法」销售VPN“翻墙”软件是否构成犯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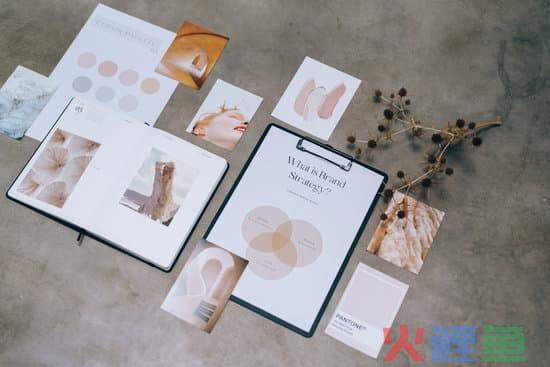
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同时,网络犯罪也如暗潮涌动,不断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翻墙”软件就出现在互联网不断发展、开放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它作为技术工具满足人们实现跨境互联的需求,另一方面它又是网络犯罪传输信息、隐蔽地址的温床。
面对已成规模的跨境电信市场,许多制销者逃避电信部门监管,代理、搭建VPN“翻墙”软件,提供跨境电信业务,谋取利润。
尽管VPN技术已在各种社会场景中得到广泛应用,但销售VPN“翻墙”软件的行为在法律界却很少得到针对性评价。
2016年,朱某(男,1988年12月29日出生)于荆州市荆州区设立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朱某创建多个网站,用以销售其代理和自行搭建的VPN“翻墙”软件。
用户通过使用该VPN软件,可以访问国内IP不能访问的境外互联网网站。2017年7月,朱某在接到公安局关停VPN业务的《网站关停通知书》后,拒不关停继续经营,直至同年9月案发。
经鉴定,2017年8月1日至当月31日、同年9月1日至当月27日均产生连接境外IP记录的会员账号数量478个。从2016年开始至案发前,朱某支付宝记录的交易额共计人民币1741620元。
被告人朱皓于注册成立荆州市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网站用于推广其代理销售和自己建立并销售的VPN软件。
用户购买该软件后,可以访问国内IP不能访问的境外互联网网站,并牟取非法利益。最终朱皓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八万元。
一、朱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
在本案中,行为人朱某于荆州市荆州区设立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并创建多个网站用以销售其代理或自行建立的VPN“翻墙”软件。
根据案件信息可知,朱某创办公司和网站,主要目的就是销售VPN“翻墙”软件,故该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应为朱某个人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该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本罪的犯罪主体,本案不是单位犯罪。
但是,朱某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在明知其行为违法的情况下,积极代理和搭建VPN“翻墙”软件并公开在网络上销售,作为已达刑事责任年龄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主观上具有故意的成年人,朱某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判断是否构成提供侵犯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的关键在于犯罪客体和客观方面的认定。本罪属于故意犯罪,尽管理论上存在是否包括间接故意的争议,但由于本罪在主观上不要求行为人具有特殊的犯罪动机和犯罪目的,朱某在深知VPN“翻墙”软件主要功能的情况下仍主动销售,其主观故意清晰明了。
本罪的犯罪客体是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对象有两种:专门程序、工具(有害性信息安全设备)和其他程序、工具(中性程序),本罪的危害行为就在于提供上述两种程序、工具。
交织于犯罪客体和客观方面之间的,也是朱某是否构成本罪的重中之重的,就是犯罪对象的认定问题,即VPN“翻墙”软件是否属于本罪中的程序、工具。
VPN“翻墙”软件以通用技术制作,被动规避GFW的审查,达到浏览境外网站、访问境外网络资源的目的,该“翻墙”软件并没有对GFW进行侵入或控制,亦没有避开、突破其安全保护措施,不属于有害性信息安全设备,即不属于“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
那么,朱某的销售行为是否属于提供中性程序,即明知有人在实施针对计算机系统的相关犯罪,仍为该人提供程序、工具呢?本文认为同样不属于。
尽管在许多网络诈骗犯罪、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计算机犯罪中,犯罪行为人都经常使用VPN“翻墙”软件隐藏自己在网络世界里的“踪迹”,但同样有许多非出于违法犯罪,而是出于生活目的使用VPN“翻墙”软件的网络用户。
本案中,朱某销售出VPN“翻墙”软件共计478人次,产生478个有连接境外记录的会员账号,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其中有账号使用者利用朱某提供的“翻墙”软件从事了违法犯罪活动,毋论从事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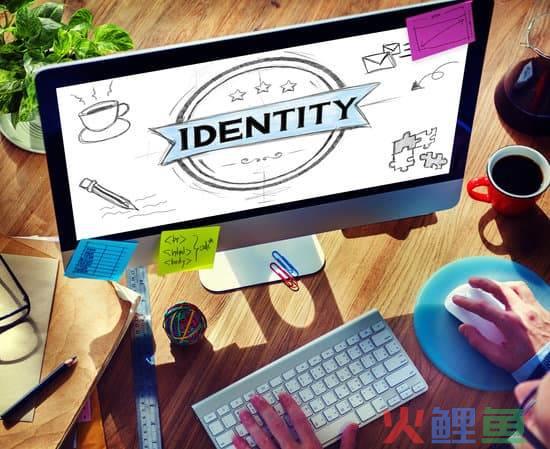
假设真有账号使用者利用该“翻墙”软件进行了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活动,尚需进一步证明朱某对此明知。
综上所述,VPN“翻墙”软件不属于有害性信息安全设备,在本案中也没有作为其他程序、工具使用。朱某销售VPN“翻墙”软件的行为侵害的不是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不应以提供侵犯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进行评价。
二、朱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是特殊主体犯罪,是故意犯罪,本罪的成立需有行政前置程序。朱某销售VPN“翻墙”软件的行为,实质上是在为所购“翻墙”软件的会员提供跨境网络接入服务,朱某的销售行为证明其属于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具有本罪的主体身份。
从本罪出发,对朱某的构罪评价主要集中在其没有按照《电信条例》的有关规定获得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以及在监管部门——荆州市公安局做出关停VPN业务的通知后,拒不关停继续销售VPN“翻墙”软件的行为上。
行政前置程序与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呈现出前后的因果关系,必须是在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实际履行或没有完整履行该管理义务后,监管部门再做出责令改正的通知,而责令改正又与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具有实质的一致性,即通知内容为继续履行该义务、补正挽救义务未尽导致的危害后果。
因此,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是构成本罪的核心要素。根据案情,朱某应申请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而未申请的行为,是否属于未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前文论证已经认定为不属于。
相反,从朱某处获得的境外浏览留存记录、会员账号数目正是朱某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履行记录保存等相关义务的体现。
由此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与荆州市公安局做出的关停业务通知无关,既不是做出依据,也不是改正内容,故该关停业务通知不能认定为本罪中的行政前置程序。
综上所述,朱某没有违反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关停业务通知书不属于本罪的行政前置程序而仅是一般性的行政处罚,对朱某的非法销售VPN“翻墙”软件的行为不应评价为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认为制销VPN“翻墙”软件的行为构成此罪的观点实为混淆了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与行政许可申请义务,其实质是对VPN“翻墙”软件制销者未履行具体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如用户信息留存等)义务的评价,不能用于评价单纯的非法售卖VPN“翻墙”软件的行为。
三、朱某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
根据《扰乱电信市场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以租用国际专线、私设转接设备或者其他方法,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进行营利活动,扰乱电信市场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本案中朱某销售VPN“翻墙”软件,为软件使用者提供跨境虚拟专网服务。
根据《电信条例》和《国际通信出入口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开展跨境电信业务必须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并取得相应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朱某在没有申请并获得批准的前提下,经营互联网国际数据传送业务和国际数据通信业务,擅自进入国际电信业务市场,扰乱了电信主管部门对国际电信市场的管理秩序,也损害了合规开展国际电信业务的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
前文所列几起因使用VPN“翻墙”软件而受到行政处罚的行政违法行为,均以违反国际联网相关规定68进行处罚,而非以违反侵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也可见一斑,打击“翻墙”软件的目的在于保护国际电信业务,非经许可不得擅自进行国际联网。
综上所述,朱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制销VPN“翻墙”软件,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在监管部门对其非法经营行为做出行政处罚后,仍然继续经营,非法所得数额百万余元,达到规定的“情节严重”数额标准,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